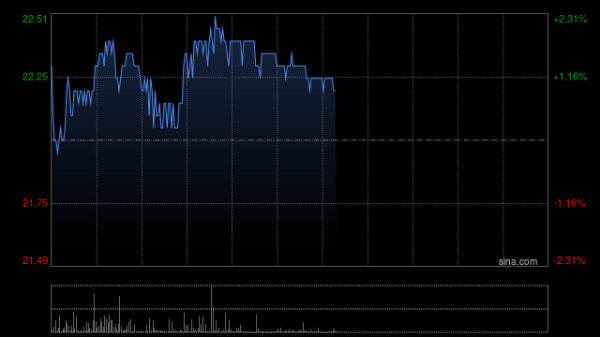文︱陆弃配资股票配资
当权力把法律当作武器时,受害的从来不是抽象的“制度”,而是那些靠制度生活、呼吸并创造价值的人,科研人员、工程师、创业公司,以及依靠高校技术转化维持生计的普通公众。8日爆出的消息,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这一点摆在了眼前:美国商务部以《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为据,要求哈佛在9月5日前上报所有由联邦资助产生的专利清单,并以“不合规”为由威胁收回或重新授权这些专利,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亿美元。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监管,而更像是一场政治清算。

先说事实。商务部长在给哈佛校长的信中明确指出,将对哈佛通过联邦科研拨款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开展全面审查,怀疑存在晚报、未遵守“实质性制造于美国”条款等问题;一旦认定“违约”,政府可以启动所谓的“介入权”(march-in rights),直接收回专利所有权或把许可权授予第三方。哈佛方面立即回击,称此举是“针对哈佛为捍卫自身权利和自由所受到的又一次报复”。从媒体综合报道看,这份信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白宫自今年初以来对高等院校施压政策的延续。
把法律搬到政治的天平上称重,本身就是一种滥用。拜杜法案诞生的初衷,是鼓励联邦资金支持的科研成果走出象牙塔、进入市场:大学可以保留专利,去寻求产业化、成立公司、吸引风投,从而把研究转化为社会福利与就业。这套机制在过去四十多年里确实推动了大量生物医药、新材料、信息技术的商业化。政府手中所谓的“介入权”,本就是一个极端、例外的救济手段,而不是日常监管的常规工具。现在政府把例外变成了常态化威胁,把法律变成了要挟学术自由、收割政治分歧的工具。
更不可容忍的是,这场行动的背景不是技术合规的单纯问题,而是广泛的政治对抗。自从白宫将“反犹主义清理”“废除按族裔倾斜的招生政策”等议题作为与高校博弈的筹码后,联邦政府已对多所名校祭出经费冻结与法律施压。哥伦比亚、布朗选择妥协并结案;哈佛、康奈尔、UCLA等则试图抗争。把科研拨款和学术议题绑在一起,等于以研究经费的生死做要挟,任何一个科研机构、一位教授,都可能在政治风向变动时成为筹码。学术独立一旦被这种以利益为诱饵的政治操作动摇,损失的不只是几项专利,而是整套科研生态与公信力。

我们必须认清两个残酷的现实。第一,大学专利并非孤立的“学校财富”,它们常常是数百、数千科研人员多年积累、学生实习、外部合作共同作用的结果;强行把这些专利收归国有或指定第三方,不仅剥夺了原始科研团队未来收益的可能,也会切断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纽带。第二,创新生态需要的是可预见性与制度信任;当政府以政治判断替代专业审查,企业投资、风险资本与创业者都会重新计算投入大学技术的成本,那意味着创新速度放缓、优秀学生与人才流向海外,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毕生研究贡献给一个随时可能被政治没收的系统。
有人会说:法律就是法律,若哈佛违反了规定,政府有权查处。这一点没错,但问题在于:执法必须公正透明,而不是选择性运用、用以惩戒政治异见。若真正关心合规,应该以程序、证据、公开听证为前提;现在的步骤却是突击性要令、威胁性措辞、并置于一连串政治诉求的大背景下。把合规问题变成政治复仇的借口,既侵蚀法治的底色,也把科研人员绑在了意识形态的十字架上。
更要警惕的是,这一招具有复制性。如果一个政府可以凭借模糊不清的“合规”指控,拿走大学的专利与技术,那么未来任何一个掌权者都可以以同样方式操作。想象一下:下一届政府基于“国家安全”“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危害”之名,要求大学上交敏感或不合其意的研究成果清单;学术成果从此成为政权稳定的工具而非公共财富。科研不公然政治化的最后防线,将在我们不警惕时轰然倒塌。

针对这一点,我有三个直白且不得不说的结论:第一,学术界必须把这次事件视作清醒剂,不再天真地认为法律会在关键时刻保护学术独立;团结、公开、法律反击,应当是高校的第一反应。第二,产业界和风险投资不能坐视自己的投入被政治化没收;技术转化与许可制度需要更坚定的市场保护机制以及多元化的资助来源,以分散政治风险。第三,公众应该认清:把科研成果置于政治争斗中,最终受损的是普通民众,无论是因新药上市延迟,还是医疗设备国产化进程被干扰,后果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成本。
哈佛的抗议词句铿锵有力,但这不是单靠一句声明就能抵御的长战。学者们要准备好走法律程序;行业要警惕并重新审视与高校的合作条款;立法层面也应考虑修补拜杜法案的缝隙,让“介入权”的使用更加透明、受限且必须通过独立司法或监督程序,而不是行政单方面宣判。
最后,别被“国家利益”的空泛喧嚣迷惑:真正的国家利益,是建立在持续、稳定的创新能力之上,而不是在政治时间窗口里靠抢夺专利来讨好选民或报复敌对的学术机构。夺取专利不是对抗学术精英的胜利,而是对未来竞争力的一次自戕。若美国以此为范式,全球科研生态都将陷入寒冬;若其他国家见风使舵跟进,全球创新链条将被碎片化,受害的仍是普通消费者与患者。
启泰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